 吴国章律师,男,1997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1999年10月份成为一名执业律师,2003年5月份发起创办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现为该所主任。吴国章律师还先后兼任莆田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员、莆田市人大内司委法... 详细>>
吴国章律师,男,1997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1999年10月份成为一名执业律师,2003年5月份发起创办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现为该所主任。吴国章律师还先后兼任莆田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员、莆田市人大内司委法... 详细>>
律师姓名: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号码:0594-2261218
手机号码:13905046298
邮箱地址:510320027@qq.com
执业证号:13503199910474166
执业律所:福建壶兰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三迪国际公馆33—34层

【内容摘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后,不论是在法律规范还是在学术界,均将“排除合理怀疑”理解为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和补充,“排除合理怀疑”没有获得独立的生命力。本文通过对“证据确实、充分”在理论基础、文义逻辑、法律体系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后,再而将“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进行比较分析,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仅是控方的证明责任,不是证明标准,只有“排除合理怀疑”才是证明标准,而且是专属于法庭的用于检测“证据确实、充分”的更高标准。唯有坚持“排除合理怀疑”是比“证据确实、充分”更高的标准,才能真正落实和巩固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成果。
【关键词】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 证据确实、充分
![]()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渊源及主流观点
理论界一般认为,全球范围内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大抵分为三大类:一是英美法系“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二是大陆法系“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三是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而且三大证明标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1。在美国引入“排除合理怀疑”之前,陪审团适用的刑事证明标准是“确定”的标准——陪审员需进行宣誓,以保证其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后才作出了真实的判决。18世纪美国引入“道德确信”的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前身。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得到美国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广泛使用,1970年的温希普安(In re Winship)判决,赋予“排除合理怀疑”以宪法地位。之后,就法官如何向陪审团解释“排除合理怀疑”——排除合理怀疑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在美国历史上,先后形成了诸如“一个合理的怀疑不是一个不合理的怀疑”“相当于确保个人生活中作出重要决定时的信念”“会使一个谨慎细心的人在行动时产生犹豫的怀疑”“对罪行的坚定信念”“一个能够给出理由的怀疑”“作为高概率的合理怀疑”“不需要阐释的怀疑”等多种解释。2在我国,“排除合理怀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主流观点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产物而被否定。近年来,随着意识形态色彩的弱化、西方法学思想的传播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我国“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困境——所曝光的大量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该证明标准导致的,理论界开始探讨、研究和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我国最早在规范性文件中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是《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表述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但最终“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被删除。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第53条正式引入“排除合理怀疑”。对于我国立法上确立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学术界有三种学说。一是“新标准说”,认为“排除合理怀疑”是与“证据确实、充分”相并列的新的刑事证明标准。比如,有学者主张,“我们甚至有理由乐观地预计‘排除合理怀疑’可以正式进入司法解释甚至刑事诉讼法而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列”3。二是“补充说”或“解释说”,认为是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解释或补充,并不是新标准。比如,有学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对于‘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在实践运行中的完善和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有一定的补充作用”4;参与立法的人员则解释称,“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而是从另一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5。三是“同一标准说”。比如易延友教授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是同一个标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前者从积极的、肯定的角度描述法官的内心确信程度,后者是从消极、否定的角度描述法官的内心确信程度。二者在内涵上、本质上是一样的”6。笔者认为,前述三个学说仅从某一维度考量“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地位,难免均有缺陷。其实,在讨论“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律地位时,不但应当将“排除合理怀疑”置于全球法制史下刑事证明标准发展、变化、融合的大背景进行考量,同时还要充分考察我国“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在实践中存在的痼疾以及“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从被排斥、热议、引入、提升的地位变化历程。在这样大背景的镶嵌下,凸显了“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用于检验、测试“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更高的新的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之批判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1979年诞生之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一直成为我国刑事证明标准。该证明标准以发现案件真相为价值目标,强调证明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性,主张判决事实、命题事实应当等同于客观事实。该证明标准为指导和规范执法人员、司法人员查清犯罪事实、惩罚犯罪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该证明标准在严格意义上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在实践中已充分暴露出其固有的各种缺陷,甚至是酿成冤假错案的制度性毒瘤。

(一)从文义解释角度看,“证据确实、充分”不是完善的证明标准。何谓“证据确实、充分”?根据裁判规则的解释,其中“证据确实”是对证据的质的要求,是指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是对证据的量的要求,是指案件事实需要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7简而言之,“证据确实、充分”就是对案件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质的要求就是证据具备“真实性”,量的要求是证据在数量上满足组成犯罪构成要件所有事实的需要。所以,“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其实只需满足两个条件:证据具有真实性和要件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证据满足“真实性”的前提是经过查证属实,也即已经排除了非法证据,实际上证据具备真实性必须经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补强规则”“直接言词规则”等证据规则的过滤,才可以推定具有真实性。但实践中证据并没有经过这么多过滤网的净化,其真实性的概率仅仅处于“优势地位”,而不可能是“确实”的。证据在量上的充分,其实就是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原理将犯罪事实瓦解成各个分散、零碎的事实片段,通过认定证据满足事实片段而认定犯罪事实成立,而不考虑事实片段在总体上是否相互关联、链接而形成无缝、闭合性的判决事实。也即,“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最大的致命弱点在于完全忽略了事实片段之间的关联性,而事实片段间的关联性却是英美法系中最主要的证明标准元素。以缪新华案件为例8,控方指控缪新华伙同他人谋杀杨某,从证据充分的角度看,在杀人动机及杀人、分尸、抛尸三个环节的事实,都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比如,在分尸环节,有五被告人供述、作案工具菜刀一把与砧板一块、包装尸块的塑料袋、尸检报告等证据,这些证据足以证实分尸事实成立;在抛尸环节,有五被告人供述、运输尸块的拖拉机、包裹尸块的浴巾、塑料袋、现场辨认笔录等,这些证据也足以证实抛尸事实成立。所以,依据“证据确实、充分”在概念上关于证据质和量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缪新华等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明标准已经达到法定标准,并没有不当之处。然而,原审判决仅顾及证据“充分性”而抛弃了证据的“关联性”。事实上,作案工具菜刀、砧板、浴巾、塑料袋、拖拉机等这么“充分”的物证与该案没有丝毫关联性,恰恰是证据的“充分性”酿成了冤假错案。
(二)从认识论角度看,“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违背了认识论的基本规律。案件事实是过去却已不存在的事实,司法人员的首要职责是发现案件真相,就是将过去发生的事实通过证据来证明、恢复和重现。虽然案件事实的发生会通过证据遗留下各种蛛丝马迹,但是证据随着时间的流逝,部分证据会变化甚至灭失,客观上就无法重现案件事实。同时因为人类认识的缺陷,无法将证据按照符合案件事实的形状、轨迹进行还原,根据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只是假设的接近于客观事实的事实,并非客观事实本身。正如学者所说的,“证据作为案件发生之后遗留下来的一些蛛丝马迹,就像一个花瓶打破后的有限的碎片,正如你无法找到所有的碎片,从而重新拼起一个完整的花瓶一样,凭借这些事实的碎片重构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或多或少的差异总是不可避免的”9。比如,在缪新华案件中,死者杨某于2003年4月6日晚上外出失踪,至同月19日在柘荣县城郊乡一废旧房子内发现杨某尸块,现场只有尸块及包裹尸块的浴巾、塑料袋、车辙、车胎印迹,此外再无任何实物证据。在该案件中,需要司法人员重构的主要事实有:是谁杀害杨某,杀害杨某的动机是什么,在何时何地用何工具如何杀害杨某,在何处以何工具如何将杨某分尸,何时以何工具将杨某抛尸,杨某的首饰和随身携带物品去向在哪。显然,根据现场的证据根本无法重构客观事实。这就是哲学上认识论的规律,人类只能认识接近于真相的事实,而不可能发现和重构客观事实。然而,“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要求的案件事实是“确实的”——100%准确概率——客观事实,显然违背了认识论的客观规律。在美国引入“排除合理怀疑”之前的18世纪,要求陪审团认定的案件事实必须是“确定的”,但那时学术界和实务界已意识到“确实”是不可能的,故而转而适用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三)从价值论角度看,“证据确实、充分”是盲目的理想目标。刑事证明标准不但要遵循客观规律,当然还要体现社会某个历史时期刑事诉讼法的追求目标。“证据确实、充分”体现的面貌似乎是客观性的事物,但其实更多地体现我国立法者的立法精神和价值目标,是国家的主观宣誓——追求案件真相,做到司法公正和不枉不纵。这种立法价值目标当然是正义,几乎接近于自然法的正义。但是,价值论总是受限于认识论,在认识论上人类无法实现的目标,在价值论上就是盲目的理想主义、乌托邦。当然,立法精神可以是应然性的,规范目的应当具有引领性,当无异议。然而,不切合实际的立法精神往往会误导司法人员为迎合立法目的而制造冤假错案。实践中,很多冤假错案不是刑事诉讼法认识论决定的,而是人为因素决定的,人为地炮制案件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制造了可以定罪量刑的假象。比如,在缪新华案件中,通过再审我们发现,有罪的证据不堪一击,但侦查机关为什么还是收集了那么多的“垃圾证据”——没有关联性的证据,这些证据在形式上能够印证每个环节的犯罪事实,让人在直觉上、意识上均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为了使这个证明标准具有无懈可击的可靠性,通过诱供、指供伪造了大量私密性的案件信息,让公众因为迷信“确实、充分”标准而得逞。缪新华案件中为何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菜刀、砧板?无非为了达到证明分尸事实的“确实”程度。然而,一把菜刀杀死一个人是没有问题,但一把菜刀和一块砧板是如何完成分尸呢?尸体可以如同一块猪蹄而在一块日用的砧板上被进行肢解吗?被告人为何非得在将尸体安放在砧板上进行肢解呢?对“确实、充分”的疯狂迷信和狂热追求,才导致违背生活常识的错乱诉讼行为。
(四)从诉讼模式看,导致庭审的形式主义。实务中,“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是通过印证规则来实现的。印证规则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形式的真实性验证。法官通过比对讯问笔录、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陈述笔录等书面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审查各类证据之间在主要事实上是否存在矛盾,以排除主要矛盾作为作为定罪量刑的基础。在缪新华案件中,尽管“各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前后不一致,呈阶段性反复”,尽管各原审被告人“关于参与分尸人员”“关于分尸地点”“关于分尸工具”“关于包装尸块的塑料袋和浴巾”“关于何人通知缪进加运尸”“关于参与抛尸人员”“关于被害人佩带首饰的去向”等事实的供述前后之间、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但关于“杀人”“分尸”“抛尸”的基本事实是一致的,能够“相互印证”,达到“确实”标准而可以被定罪。二是要件的充分性验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4条规定,对于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事实,应当是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而有罪的事实,是指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由被告人实施,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及案件起因等。法官可以根据前述构成要件事实的清单,逐一核对是否有相应的证据。如果每个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都有证据支持,则属于证据充分。比如缪新华案件中,法官需要的每个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据,控方提供得很“充分”,杀人环节有“用右手掐住杨某脖子”,分尸环节有菜刀、砧板,抛尸环节有拖拉机,等等。三是证明的逻辑性验证。从证据事实到案件事实是一个运用逻辑原理进行证明的过程。控方呈现在法官面前的是假设的案件事实,或者说是命题事实,这个命题事实的证明过程是否符合法律、逻辑、经验和常识,需要法官验证。法官完成了证明的逻辑性验证过程,就是认可案件事实的过程。
不论何种验证内容,印证规则的实质是以卷宗主义为基础的书面审理模式,法官流连于卷宗材料而不是直接言词证据,迷恋于卷宗材料中书面证据的精致性而不是合法性,专注于证据充分在数量上的物理性、数学性而不是关联性。于是,庭审就是“走过场”,被告人当庭辩解、“翻供”只是法定程序中的应景环节,证人不出庭是常态,刑事诉讼的重心在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加工阶段”,庭审只是对“加工”的证据“产品”进行“验收”,庭审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在缪新华案件中,假如合议庭运用的不是“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而是审查言词证据的合法性与实物证据的关联性,那么,该案在原一审、二审的证明标准就不会达到“事实清楚”的定罪标准。比如,虽然被告人供述了杀人、分尸的工具是菜刀、砧板,可是菜刀、砧板上并没有五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生化物质;虽然供述了裹尸的物证是浴巾和塑料袋,运尸工具是拖拉机,但这些物证同样没有五被告人及被害人的生化物质。
(五)从证明责任看,造成证明过程的机械论。我国新法定证据主义表现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在实体方面,有罪证据必须能够覆盖犯罪构成要件所涉及的全部事实,具体而言,按照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进行核对证据“物件”。在程序方面,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根据满足实体要件所需要的证据开具证据清单,按图索骥,拼凑齐全;第二,所搜寻的证据必须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在新法定证据主义下,证明过程的客观性被强化,也更加精细化,事实与证据只是需要与被需要的呼应关系,而不是证明与被证明的逻辑关联关系。从证据到事实的证明过程,只是检验证据形式真实性与数量要件性的过程,相当于标准件生产线上的流水作业,法官不需要主观能动性,更不需要社会经验和生产常识的参与。
(六)从实证角度看,造成冤假错案。“证据确实、充分”确定的是100%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上将,可以认为认定的案件事实几乎接近客观事实,判决结果100%是真实有效的。在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前,我国都是适用“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定罪量刑的,可是,大量的惊天冤案错案假案恰恰就在那时形成。面对这些已纠正的冤假错案,我们不禁要质疑,同样的证据、同样的程序和同样的法律,为何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结果?是哪儿出现了问题?毫无疑问,是“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出了问题!在缪新华案件中,在案证据材料按照“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来评价,完全符合该标准。首先,就“证据确实”标准而言,在言词证据方面,原审被告人供述均承认了“杀人”“分尸”“抛尸”的事实,供述间相互印证,是真实的,达到“质”的“真实性”标准;在实物证据方面,实物证据系被告人提供的私密性证据,具有客观性,也达到“质”的“真实性”标准。其次,就“证据充分”标准而言,起诉书指控的所有犯罪环节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达到“量”的充分性标准。同样,其他诸如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杜培武、张氏叔侄等冤案假错案都是因为这种证明标准形成的。究其原因,是该证明标准在“三性”方面出现了问题。刑事证明标准其实是证据可采性标准的综合与提升。证据可采性标准即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三性”标准,但“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实际上仅考量证据的“真实性”,抛弃了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标准,以至于法庭允许将“非法证据”“带病的证据”“垃圾证据”冲量进入法庭,法庭不需要对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怀疑,绕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言词规则、关联性规则等实质化庭审活动,审判活动仅是配合控方对控方提供的证据和指控的事实进行司法确认而已。
排除合理怀疑——检验证据确实、充分的更高标准
讨论“证据确实、充分”在逻辑上存在的漏洞、在理论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全盘否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而是通过梳理和反思该标准于正确理解和评价“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律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既然“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具有天生性的疾病,刚刚引入的“排除合理怀疑”断然不可能与之站队,否则,“排除合理怀疑”就失去了在我国生存、发展的生命力。多数学者主张,“排除合理怀疑”不是新标准,与“证据确实、充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是原标准的解释与补充,果真如此吗?如果是这样,“排除合理怀疑”于“证据确实、充分”而言,是换汤不换药,而仅仅是换成事物的另一面就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司法实践难题吗?我们司法实务者的思维是这么僵硬吗——僵硬的无法涉及同事物的另一面?理论界的思想这么固执吗,用了200多年来承认属于同一事物的另一面?立法者的胸怀这么狭隘吗,用了30多年来吸纳同一事物的另一种说法?10可见,“排除合理怀疑”所应有的法律地位并非理论界普遍认为的如此之简单,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其旺盛的司法生命力和司法理性并安放于合理的法律地位,才能正确引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

(一)对法律地位现状的反思。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而“排除合理怀疑”是其中条件之一,为此,立法者解释称“排除合理怀疑”是对“证据确实、充分”反方向的补充。甚至从逻辑解释角度看,相对于“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处于从属地位,附属于“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但是,从文义解释角度看,“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前面两个条件其实仅是重申“证据裁判规则”,而不是证明标准的特有内容,只有第三个条件即“排除合理怀疑”才是证明标准的应有之义。如果不考虑证据裁判规则,《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最终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从实证角度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已经获得独立的司法生命力。在缪新华案件中,再审判决对单项证据材料和综合全案证据材料的认定,均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比如,对于被告人有罪供述,再审判决认为,“在有罪供述中,各原审被告人承认杀人、分尸、抛尸的主要事实,但又对分尸地点、被害人佩带首饰去向等事实情节供述不清,不合理,且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之间的矛盾亦未得到排除……故各原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及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综合全案证据,再审判决认为,“有罪供述和现场勘查笔录之间均存在无法合理排除的矛盾和疑点……且其他定案证据亦存疑”。可见,至少从立法或实践来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实际上处于解释甚至替代“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地位。
(二)是检验“证据确实、充分”的更高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是一种构建式的证明结果。控方好比是建筑师,“证据确实、充分”好比施工图,建筑师根据施工图的要求将各个建筑物件搭建起来,控方也根据“确实、充分”的施工图将相关证据材料组合起来,构建起指控的犯罪事实。建筑师根据施工图纸进行施工,不等于说其完工的工程质量就是合格的,是否存在遗漏施工内容,是否漏水,是否达到抗震要求,等等,都必须经过验收程序以确认工程质量是否合格。验收的标准不仅仅是施工图纸,还有国家制定的技术规范标准等。同样,对于控方完工的犯罪事实搭建是否合格,也需要法庭进行验收,法庭验收的标准就不能是单一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因为该标准仅是施工图纸,仅作为验收的参照物,不能作为验收标准,验收标准应当是某个能够涵盖检测单个证据的“三性”,检测证据之间、事实之间闭合性,检测证明结果唯一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所以,“证据确实、充分”是一种构建式的证明过程,根据证明责任要求控方需在刑事诉讼图纸中填充各种证据物件,填充完整则视为尽了证明责任。而“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瓦解式的证明过程,对控方填充的各个证据物件进行反向核查、推敲,试图瓦解、推翻控方已构建的命题事实。如果不能瓦解,则指控的事实是可以进行司法认定的事实;如果可以被瓦解,则指控的事实不能成立。因此,“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检测“证据确实、充分”的更高标准。
从诉讼职责分配理论看,控方负有构建式的证明责任,而审判人员只是居中裁决,判断控方的构建式证明过程是否符合法律、逻辑、经验与常识。显然,法官的判断标准(证明标准)不应当等同于控方的证明标准,如果法官的证明标准等于控方的证明标准,法官实施的也是构建式的证明过程,违背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职责,而是取代控方的指控职责而行之。所以,从诉讼职责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处于高于“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地位。
“排除合理怀疑”的特有性质也决定了其标准高于“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证据确实、充分”强化证明程度的客观化,是一种客观证明标准11。但刑事证明过程必须通过法官的认识、常识、学识进行分析、论证、推敲,是一种思维活动的过程,是主观对客观进行评价的过程,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客观性背离了刑事证明过程的认识论规律。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在遵循刑事诉讼认识论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了法官在认识上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的“怀疑”是符合常理、有根据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胡乱猜疑。12
综合以上各个角度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所无法比拟的,不应当被理解为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更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解释和补充。
为形象论证“证据确实、充分”的构建式证明过程与“排除合理怀疑”的瓦解式证明标准的区别,笔者以构图形式进行说明。具体见图1、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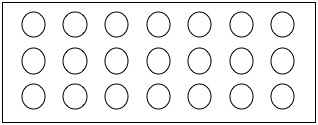
图1
大方框代表证明最大范围
小圆圈代表满足证明范围的证据物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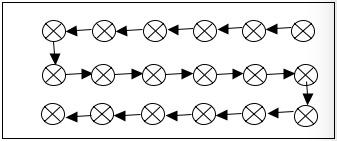
图2
→代表法庭核查证据“三性”
×代表瓦解在案证据、事实
(三)是专属于法庭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不仅是检测“证据确实、充分”的更高标准,而且是专属于审判阶段的定罪标准。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制体现的是“证明标准同一论”,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刑事诉讼的三个阶段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证明标准同一论”不但背离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也是导致庭审形式化的制度禁锢之一。只有破解“证明标准同一论”,方能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条、172条和195条的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均应当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而“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是“排除合理怀疑”。2016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院部联合发布并实施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2条也规定,“侦查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都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认定证据,依法作出裁判”。2012年《刑事诉讼法》引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后,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也相应修改了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3条以及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6条就“证据确实、充分”的三个条件,作出与《刑事诉讼法》第53条完全一样的规定。以上规定体现了“证明标准同一论”的观点,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有罪案件事实的审查与认定,运用的是同一个证明标准。然而,笔者认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尤其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专属于法院的刑事诉讼活动和诉讼规则,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不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1.“证明标准同一论”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就是说,在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判决有罪之前,对被告人指控的犯罪事实都是假设的事实,是命题事实,并不是“确定”的事实。然而,“证明标准同一论”却表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其所认定的犯罪事实已经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排除合理怀疑”的“确定”标准;也就是说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是确定无疑的,对其定罪的条件已经和判决有罪的条件是一样的。显然,“证明标准同一论”是“有罪推定”的产物,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2.“证明标准同一论”混淆了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将案件提起公诉,均是各自依法依职权决定的,并不需要向法院或其他任何第三方证明什么,“不存在证明标准的问题”13,其涉及的仅是证明责任问题,即控方如何遵循认识论规律收集、固定所有案件证据,尽了应尽的证明责任,这种证明是自向证明,“是自己证明给自己看”14,是自我论证并自我调整案件事实的过程。即使将其称为“证明标准”,但只是一种自我要求的内部标准,并不对外发生“确信”的法律效力,严格来说仍属于认识论范畴。比如在缪新华案件中,如果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认为缪新华案件的犯罪事实已经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只是自我评价而已,该“证据确实、充分”并不对嫌疑人、被告人发生法律效力。
3.“证明标准同一论”导致庭审形式化。在坚持“证明标准同一论”的语境下,控方提起公诉的案件的犯罪事实既然已经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而且,控方所适用的该证明标准与人民法院适用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那么,法院就无需重新对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审查与论证,无需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质疑,控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已经被赋予天生的“确定”效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架空,直接言词规则被搁浅,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被冷落,辩护权、对质权被限制……庭审程序就是形式化、走过场,不存在庭审实质化问题。而如果法律没有赋予控方指控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效力,法官失去了对审前证据“三性”标准的依赖性,当然需要审慎对待控方指控的事实。法庭需要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审查每个单项证据和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发现案件真相的固有职责必然驱动法官将庭审实质化。正如念斌案件,“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不予核准死刑发回重审后的二审庭审可谓庭审实质化的标杆。此次二审的两次开庭,12名公诉人参与,31人次出庭作证或说明,6天5夜60小时的庭审,每个出庭人员平均接受交叉询问近1小时,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辩方对证据进行刨根追底的追问,双方专业人员对检验结论进行深入分析解读,使法庭真正成为审理案件的中心”15。
【结束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仅仅是控方的证明责任,而不是证明标准。控方的证明责任是控方自我约束、自我评价的机制,没有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控方无需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才是证明标准,而且是专属于法庭用于检测“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唯如此,方能彻底强化和巩固庭审实质化,方能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改革政策。
![]()
注释和参考文献
1、陈卫东主编:《刑事证据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2、 [美]拉里劳丹:《错案的哲学——刑事诉讼认识论》,李昌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5页。
3、陈卫东主编:《刑事证据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4、沈志先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104年版,第329~330页。
5、郎胜主编:《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102年版, 第115~116页。
6、易延友:《证据法学—-原则·规则·案例》,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616页。
7、李慧群:《郑福田、傅兵抢劫案——对共同犯罪案件如何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载《刑事审判参考》(总第86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4页。
8、详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刑再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9、汪建成、孙远:《自由心证新论——“自由心证”之自由与不自由》,载《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编写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11、江必新主编:《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12、同注释5。
13、同注释4,第335页。
14、罗国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定罪标准》,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9期。
15、沈德咏:《庭审实质化的六项具体改革措施》,载《法制日报》2016年2月3日。
本文获2018年福建省律师实务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转载需注明来自壶兰律师所哟~![]()
![]()
壶兰所感谢您的关注,期待您的到来~

免责声明:本网部分文章和信息来源于国际互联网,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和学习之目的。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立即联系网站所有人,我们会予以更改或删除相关文章,保证您的权利。
Copyright © 2017 www.ptdl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方式:0594-2261218;139-0504-6298
联系地址: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三迪国际公馆33—34层
技术支持:网律营管